原标题:一次对“旷野写作”价值的重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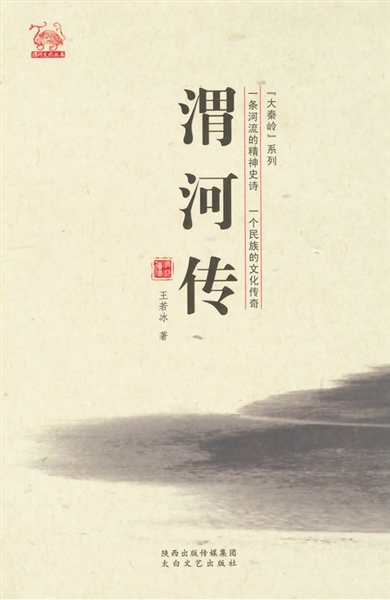
《渭河传》王若冰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第2次印刷

王若冰甘肃天水人。诗人,作家,秦岭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水市文联副主席,天水日报社副总编,天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出版、主编诗歌、散文、文艺评论十余部。主要作品有诗集《巨大的冬天》,“大秦岭”系列《走进大秦岭》《寻找大秦帝国》《渭河传》《仰望太白山》,电视纪录片《大秦岭》等。
从2004年肇始,王若冰为自己确立了“一座山,一个民族,两条河流”的宏大写作计划。一座山指秦岭,一个民族指秦人,两条河流指渭河及汉江。落实到文本层面,它们依次对应的是《走进大秦岭》、《寻找大秦帝国》、《渭河传》以及行将完成的《汉江笔记》。
《渭河传》出版于2013年底,2014年4月第2次印刷,这也是王若冰孕育时间最长的一本书。今年3月12日,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渭河传》研讨会,再一次让王若冰以及这本书走进读者的视域。
2011年8月中旬,在一辆借来的红色“猎豹”的马达声中,王若冰关于“集中而完整考察渭河流域”的行程终于得以动身。彼时,微博和微信都还没有流行起来,从他博客图文推送的“直播”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固定形象是: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身着被汗水打湿的短袖衫,肩挎巨大的相机包,手握一瓶矿泉水,泥水从鞋底翻卷上来漫过鞋面,眼睛圆睁如负轭的牛……这便是路途中的王若冰。让人不禁想起西部诗人昌耀笔下“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的情状。
“由于多年来对渭河的关注与思考,这次渭河之行,我侧重于以一种持续完整的行走与触摸感受古老渭河在我精神和内心所呈现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俯视与探寻。为了整体呈现渭河古老博大的历史文化精神,我跑遍了甘肃、陕西、宁夏三省区,包括十数条支流流经的渭河流域广大区域;我也查阅了沿途各县区的志书,走访了还遗留着渭河古老情感经历的村镇古道、历史遗迹,并从多达数百万字计的文史资料里,寻觅渭河留在中国数千上万年历史中的古老回声。”《渭河传》后记中,王若冰如是说。
故此,作家马步升认为,王若冰的散文是“走出来的”。“由于散文这种文体本身边界的模糊性,是否敢于对边界地段展开突破,是否真的有所突破,突破幅度的大小,这种突破是否具有文体的、认识的、美学的价值,正好成为检验一个散文家的考场。王若冰自觉地给自己设计了这样一组考题,他也模范地完成了这种自我测试,从而实现了自我超越。这一切,根源于他的不懈行走,和行走中的苦心思考。”这种打破散文约定边界、“泥沙俱下”的写作,在研讨会上,王若冰的同乡、诗人张晨称其为“全要素写作”。
一定程度上,王若冰的行走不仅仅是资料收集的过程,还在于对自己书斋经验的一次重审与印证。或许,只有当渭河沿岸的泥土紧粘于脚底,在滞重的步幅中,他才真正找到了叙述的自信,才抵达了自我理想写作状态的秘境。批评家谢有顺曾提出“旷野写作”的命题,他说,旷野写作就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在大地上行走,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
照此而言,王若冰包括《渭河传》在内的“大秦岭”系列的书写,无疑是对旷野写作向度及价值的一次回应和重申,尽管这种回应可能不是出于批评家的理论指引,它更多来自王若冰自我写作困境的突围与文化自觉的召唤。
经历了对渭河流域几乎全景式考察后,王若冰承认,“面对和秦岭一样沉智伟大的渭河来说,愈是对她非凡身世关注久了、思考深了,就愈觉得她负载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情感过于古老、凝重、丰富多彩;以我原有的线性思路,如果顺着渭河干流流向从渭源县鸟鼠山到渭南潼关走下去,是不足以发现并理解渭河古老凝重、丰富辽阔的精神世界的。”
王若冰:渭河既是我言说的对象,也是表达我体认的喻体
兰州晨报:你是以诗人的面目被读者知晓的。在此次研讨会上,评论家唐翰存认为“大秦岭”系列的书写拯救了你的写作,至少在写作方向上如此。你是否认同?可否简要回顾一下你与秦岭文化结缘的前前后后?
王若冰:翰存的发言可谓一语中的。我写诗很早,持续而激情的诗歌写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也在国内诗坛浪得一点虚名。同时,我是一个习惯反思反省的人,应该是在我迄今唯一一本诗集《巨大的冬天》出版前,我就在思考自己原有写作的方式、价值和意义——我总觉得开始于八十年代的极端个人化写作难以承担这个裂变时代的精神情感,我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宏大的精神文化背景,开拓自己写作新视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这种想法愈来愈强烈,为了调整这种焦灼、迷惘情绪,我有意识放缓了诗歌写作速度,更多地投情于原本我就熟悉并自觉另有滋味的评论、散文写作。直到2004年,莽莽秦岭突然浮现在我面前,我苦苦寻觅了将近十年的彷徨之路才豁然一亮。接下来的情况关注我的读者都知道,在《走进大秦岭》出版和以《走进大秦岭》为蓝本的八集纪录片《大秦岭》播出后,不仅“秦岭是中华民族父亲山”概念迅速得以普及,秦岭旅游热和秦岭文化研究热潮一夜之间走红并且持续至今,我的写作视野也豁然开朗、写作天地更加辽阔。所以翰存说“大秦岭”系列拯救了我的写作一点不为过。因为从完成《走进大秦岭》后我就发现,我很幸运地找到了适合我、可供我享用一生的写作天地。
兰州晨报: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一些资料完全可以坐在书斋得到,当初为何决意要选择“行走”甚至“苦旅”的方式亲身走一遍?这样的亲历是否改变了你最初的写作构想?
王若冰:事实上,持续十多年秦岭南北的行走写作,改变并丰富了的不仅是我的写作本身,还有我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态度。对于写作来说,最明显的莫过于进入秦岭之前,我为自己将来完成的作品取好的书名是《秦岭批评》——一看书名就明白,当时我试图延续盛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思文学”余响,借助秦岭反思并批判传统及传统文化。然而进入秦岭后,我所看到、听到、触摸到的一切却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思路。最后的结果是,脚踏实地的行走与亲历,让我从大秦岭的批判者一夜之间转为大秦岭的膜拜者、歌颂者。
兰州晨报:我们注意到,《渭河传》一书始终有“我”这个第一称的介入,但在渭河畔长大的你自始至终没有提及自己有关的童年记忆,而这一经验往往是作家们惯用的方式。是否因为类似的个体经验与本书的宏大叙事之间难以平衡?或者出于其他考量?
王若冰:说我在渭河边上长大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我老家在渭河南岸山上,要真正感受雨季到来渭河浊浪滚滚的壮观,还要赶十几公里山路。“大秦岭”系列写作主旨本来就定位在给高山河流立传并以借此探寻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根源上,这样的大题材往往在时空上要穿越上下几万年,我不可能面对一座见证一个民族兴衰沉浮的文化圣山和一条负载了一个民族沧桑史的河流抒发自己一己之幽怨的。这几本书里我所急于诉说的,是我对一条河流、一座山脉、一个族群文明史的认知和思考,所以更多的时候我需要有意识克制自己的个体情感——即便如此,读者还是不难发现,我掩饰不住的情感时不时会喷薄而出。至于行文中经常出现的“我”,既表明我的写作姿态——那就是我是在行走中写作,更是为了强调现场感,即作者与读者同时在场。
兰州晨报:在本书最后一节《远去的乡土》,你笔锋急转,落脚于现实关怀的层面。可以理解成“卒章显志”吗?换言之,这是否是你为渭河立传的初衷?
王若冰:是的。《渭河传》写作初始我就确定了借助渭河沧桑千秋变迁,映现中国农耕文明由盛而衰历史过程主题。渭河的变迁史亦即中华民族的沧桑史,渭河既是我言说的对象,也是表达我体味与认知的喻体。面对宋明以后渭河流域自然生态日趋恶化,以渭河文明为标志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日渐式微的历史,面对我们正在经历的城市化步伐正势不可挡地将维系一个民族精神血脉的乡土精神彻底摧毁的现实,隐痛、惆怅、弥望几乎伴随着《渭河传》后期写作全过程,既是为了“卒章显志”,更是为了倾诉对乡土中国依依难舍的怀恋之情,才有了原本没有计划在写作提纲之内的《远去的乡土》。
兰州晨报:目前,你对汉江流域的考察是否完成?有没有相应的写作计划?
王若冰:对汉江的考察已经于2014年分两次完成,《汉江笔记》的写作已经开始。《汉江笔记》是“大秦岭三部曲”的最后一本,由于单位工作十分具体、压力非常大,只能利用节假日挤时间写作,进度非常慢,但无论如何我得在年内完成。《汉江笔记》完成后,它将和《走进大秦岭》、《渭河传》共同组成我12年来不舍昼夜、苦苦经营的“大秦岭三部曲”。
文/兰州晨报 记者 张海龙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