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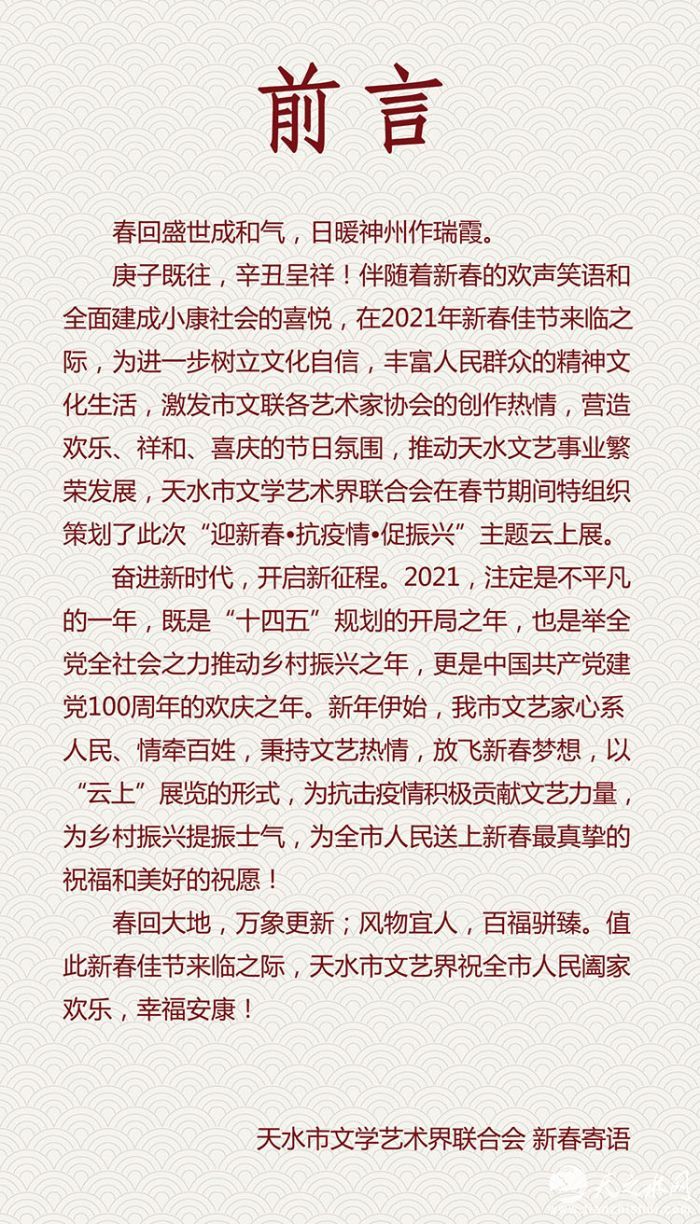
无力蔷薇卧晓枝(外一篇)
文/北方
“无力蔷薇卧晓枝”出自秦少游《春日》。全诗:“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描写的是春晓晴雨后的庭院景致。皆因诗人贴了婉约派标签,颇受后人诟病。最为愤青当属金代元好古,批道:“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其中退之山石句,指的是韩愈《山石》中“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同是描写新雨后的诗句,风格却是迥异。若单就这两句的感官入目讲,秦观的新雨却在韩愈之上。试想,夜雨初霁,那庭院中沾满雨露点点的芍药和蔷薇,恰如玉人两枚,一如满含春泪,一如无力娇卧。这样的场景与那赤脚呆坐古寺石阶上直了眼瞪着肥硕芭蕉叶子落雨的糟老头子比之,哪个动容?再者,不去考虑两者景致、人生际遇和风格特色的不同,只刻意用韩愈贬抑秦观,大为不妥。或许那庭院中,原本就只植了芍药与蔷薇,无松无柏无竹梅,秦观只是很写实主义的浪漫了一下,发个感慨,便有人用“芭蕉叶大栀子肥”来举证秦观雄性荷尔蒙分泌不足,真是做了个冤大头。
韩愈也写过蔷薇:“榆荚车前盖地皮,蔷薇蘸水笋穿篱”。只可惜,蔷薇只在一种特定状态下与榆荚、车前草、竹笋一同混杂罗列的,就象路人甲、路人乙一般作配角,自然着墨清淡,难言深意。与秦观同工的是南宋陈造的“篱头蔷薇花,娜娜新妇头”。将披散栖附于篱头的蔷薇枝叶,比作新妇头,或疏或密的蔷薇花恰如插在新妇头上,景致倒有几分动人,但这“新妇”之喻过于直露。秦观喻佳人,只写了蔷薇的“无力”与“卧”,娇好女子的柔美妩媚,连同那新雨后的清新可人,便已跃跃然撞入心扉,招惹出了一片无限的爱怜。而陈造对自己的“新妇”却心怀了一百个的信心不足,只得为伊强作了前缀修饰“娜娜”,不料反落得艳俗粉脂味道十足了。
北方的蔷薇初夏时节花开最盛,依着繁茂的枝头,并不加以拘束,色彩炫丽丰富。现代人则赋予了蔷薇花颜色不同的寓意。白色象征纯洁的爱情,黄色象征永恒的微笑,红色象征热恋……但胭脂和曙红这两种色彩,总像最美的一抹风景,不经意间就能打动人心。《诗经•郑风》中“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木槿初绽的点点胭脂水色,比做了少女脸上的一抹红晕,景象动人,却又瞬息褪色,催人倍加怜惜。《诗经•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盛赞了桃花盛开如火灼灼然娇艳美好,只是花开一季,谢了便“零落成泥碾作尘”。独这个色系的蔷薇,花期恰也是很短,即便开到最盛了,仍然在热烈中多存了几分内敛。同样,它们的宿命也终如“舜华”、“舜英”以及“桃之夭夭”一般,“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如果将这种美艳娇弱,能与后世林家小姐的有心联系到一起,搞个“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添几许凄婉,这样也最美不过了。其实这些只是自己的感受罢了,或许蔷薇中“野”的味道更为浓密,使得同为一属的玫瑰更受人青睐。
我栖居的城市里南方的因素居多,充沛的雨水尤适于蔷薇。居住区里就有很多,繁茂程度可谓惊人,它们会攀过临街矮墙,用茂密的枝叶筑起一道绿色的花墙,然后将花儿尽情地铺洒在墙里墙外,这种景象,往往令人有置身城阙之外的错觉。初夏时节,偶尔我在会顺着这些盛开的蔷薇牵引,走近它们,静静地看着在枝条上由这些柔弱和美丽所构成的一道盛大繁华的视觉庭宴,总能从心底发一声由衷的惊叹。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她们,但她们又总能将我的心绪牵引回并不适于蔷薇生长的故乡,于是许多原本隐约的情节在这些寂静的喧闹中,变得愈加清晰了。
故乡的蔷薇始自于懵懂的记忆,在母亲单位空旷的花园里就有一株被称作为“刺玫”的蔷薇花,从第一只苞蕾绽开,便如云霞栖落枝上,长久孤寂落寞惯了的灰色院子里,忽然间就被这小小艳丽染上了生气。我那时并不懂得去欣赏,看着母亲偷偷剪下了一支,插在桌上的水瓶中,任那些紫红花瓣慢慢干枯萎缩成了焦黑色,其间我只是曾经无心的去用嗅觉关心一下而已。父亲则是很小心的将那些枝头上即将谢落的细碎花瓣收集起来,盛在玻璃罐头瓶子里,腌上白糖密封了,待到瓶子的底部沉积出许多玫瑰色的液体时,用小铁勺小心翼翼地箅出,滴在白糖上做馅,那种小糖包出笼后轻咬一口所沁染到心的香甜与幸福,至今飘荡在唇舌间的记忆里。余下的固态物质,半干后切成了丝,做了点心的馅料,亦成了一代人贫瘠的童年时代过大年莫能忘怀的“年味”之一。而更多的蔷薇记忆片段已经与蔷薇无关了,或是有青涩少年初恋季节中的无奈驰往和如今渐远渐浓的故土情怀所混合出的一种味道,幻化成了我胭脂水色般的蔷薇情结,有时竟像故乡戈壁上夏暮迟日初坠时瞬间铺洒一身的霞辉,总能反复萦绕入梦。我常想,这些与那些都与眼前的“其华灼灼”有联系么?
不过,“无力蔷薇卧晓枝”的确多了几分凄怨。尽管蔷薇花儿娇艳易落,但的骨子里所带有的旺盛向上的生命力,使得它们总能从钢筋水泥丛林的间隙中,始终能以强韧性格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不断的怒放。而秦观的描写,是从他所关注的角度去入手的,也是忠实于自身的感受,这也无可厚非。若是处处强要“醉里挑灯看剑”,夜夜须得“梦回吹角连营”,此便有足够理由打发去精神科,该瞧瞧有无强迫症迹象了。
我曾经临摹一幅敦煌壁画,看着体态婀娜的“供养菩萨”兰指轻托盛开的莲花于胸前时,就将这“拈花微笑”牵强的与蔷薇花扯上了关系。《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云“尔时世尊即拈奉献金色婆罗华,瞬目扬眉,示诸大众,默然毋措。有迦叶破颜微笑……”。佛经中的“金婆罗花”专指莲花,本与蔷薇风马牛不相及。但有禅云:“青青翠竹,尽是妙谛;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或许,从这个角度讲,当你认定了,便无需再去分辨“拈花微笑”抑或“天女散花”中此花与彼花了——有时候,有心或无心比此花与彼花更重要。但现实往往锻造了我们最坚硬的部分,许多身边左右的美好和能够触动心底柔软的东西,正在熟视无睹中流水东去也。可悲的是我们总是能够籍以生活的步履匆匆,来为我们的忽略做个华丽招牌。
且听诗人西格里夫•萨松怎么说——“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应折柔条过千尺
曾经在仲春夕照下,闲坐苏堤,静品过李叔同的“看明湖一碧,六桥锁烟水。塔影参差,有画船自来去。垂杨柳两行,绿染长堤……”觉得西湖的柳,便是江南婀娜女子,最是善解人意,有千般的惆怅别怨亦是思乡念旧,都能娓娓道来与她倾听,总能与这兰舟溪桥、泉寺禅茶以及吴越春秋、断桥柔肠编织成一缕缕细密的江南烟雨柔情。许是“南方有嘉木”,身处江南,总有随心而生的淡淡愁绪,又终能和着烟柳杨花被浸润成一抹浓淡相宜的水墨诗画。
但边塞诗句中出现的北方柳色,少有了江南杨柳的柔曼身姿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的烟雨熏风味道,却多了几分萧杀。
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写秦故都柳色,清新朗润,但随后的劝酒词“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把边塞比对的鸟不生蛋了。而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写柳次之,重点放在“何须怨”上,借了婉转的呜咽声埋怨塞外迟归的春,用一种无可奈何来拓宽情绪空间,陡添了几多荒芜。加之两首诗分别提到阳关和玉门关,着墨不多,但只用到这两个特殊地标,就能联想起西北边塞时空地域交错的旷古苍凉。想必读这种边塞的柳色,着实悲恸。
我生塞外。从儿时记事起至成年离开,压根就没有身处“边塞”的概念,也从未将诗词中的种种悲凉与家乡联系起来。大概是我天生没有诗人的悲悯潜质,抑或身处简约单调中,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自然不能从雄关古道边心生出诗人的若干种种情愫。也许,其中还有塞外柳的因素呢——家乡旱柳和红柳居多,杨柳则被称作“垂柳”,主要是景观柳。印象最深的就是旱柳(也称“左公柳”,传为左宗棠西征时栽植),它们好象并无羌笛的怨妇情结,倒让诗人的悲切在我心中烙下了疑惑印记。
柳是童年记忆中的一番柔情。儿时春日,自打嫩嫩的绿色把柳树芽胞顶破,就猴急着攀树折柳,回来坐在门槛上耐了性子拧“迷迷”(家乡的孩子把柳笛称作“迷迷”),轻轻抽出嫩白柳骨,放在嘴里咂吧咂吧嫩甜的汁水后轻轻敲着念念有词:“迷迷迷迷响当当,老爷坐在板凳上……”。柳笛做好了就整日不停的吹,欢乐响亮但却单调的“音律”实在让大人们听的心烦了就大呵一声:“别吹了,招臭虫啊?”才就咯咯笑着跑散。一个盛夏记忆中,祁连山融水像野马一样在干涸了半年的河床上奔流。伙伴们瞄着对岸传说中的“唐僧白马塔”(实为纪念北凉高僧鸠摩罗什死去的白马而建),煞有心思地描述对面河滩上种满了成片的西瓜……那种炎日下吞咽口水的诱惑,着实让人无法自拔,于是就忘了父母的告诫去偷偷泅渡。结果西瓜没有吃到,当我从红泥汤汤中爬回上岸,父亲突然出现在眼前,一向温蔼的眼神忽然阴郁,用一把捋光了叶子的柳条雨点般抽打过来。我嚎叫着踮着脚尖在滚烫的沙滩上狂跳,乱舞的双手不知到底能去遮护裸露的脊背呢还是光溜溜的屁股……这些记忆,后来讲于妻儿,让他们笑得直不起腰。
柳于成年人却有不同的用场。端午节过,气温直逼盛夏,大人们会用斧子毫不吝惜地从房前屋后的柳树上剁下许多柳枝,在房檐前搭个凉棚,略带苦味的清凉就在小院里洒落一夏。手巧的男人专挑许多粗细均匀、苗条修长的柳枝,晚饭后和邻里拉着话儿间就像变戏法般一会儿编个菜篮一会儿编个精致的柳条盒子或是盛放粗物的柳条筐。自家留过一个,其它都送与邻里,引得身边围了一圈的大小媳妇们边夸赞边数落自家的懒男人,窘得巧手男人像大姑娘一样低头不停地搓弄着黑绿色的手指。如今这些印象已在记忆中逐渐地淡黄,但偶尔记起时,却多了许多值得反复咀嚼的欣悦和温情。
成年后也感受过更多的他乡柳色,了解了不同的关于柳的习俗,越发地让我对这种遍布于南北的乔木有了异乎寻常的钟爱,也格外地喜欢江南的杨柳春色。但江南离我遥远,纵使我有浸淫其中感受“点点离人泪”“愁杀渡江人”的奢望,都却因为天地南北的隔山隔水实在变得牵强。而回首落居塞外的旱柳,高大茂盛,枝条密密地倔强向上,与黄沙、烽燧、蓝天、阳光融合为一个整体,构成的柳色景致虽然与江南有别天壤,但却默守着一晨一暮周而复始的春秋荣枯轮回,和古关隘、汉长城以及石窟、佛塔等等那些古老的地域符号遥相呼应,终成一种守望。
于是,我寄望于历经夺目繁华后,宁愿回头这片沧桑,其中所有的沉淀之美。
这一年,我生活的城市里的柳绿,始于突如其来的春燥和漫天席卷的黄色尘霾,全无往昔的清新朗润。故乡的父亲在开春后右侧身体忽然失力,至省城治疗间,我乘坐大巴往返于省城和我的城市。渐渐地,隔着车窗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季节自北向南渐次进入春天,但窗外的柳色似乎因我的心境而格外遥远失实。待到柳色慢慢浸染了医院康复中心前杨柳枝条上的一日,父亲输完液偷偷溜出病房,从偌大的城市转辗寻访到了久未谋面的好友徐老先生。病中的徐老感慨间提笔以五言诗句相赠。父亲亦作回赠,却怎样努力都无法将自己名字最后的几笔流利地书写出来。我见了顿有隐痛在胸,这就是当年那个硬笔草书写得龙飞凤舞的父亲么——不期流走的岁月偷偷地让父辈们步入了耄耋,我亦与故土渐行渐远,尽能想起的故土春色只限于幼年的青青柳色和呦呦柳笛,现今的景象真的无从认知了。而更多的东西,在我一边努力苦苦挽留中,一边又偷偷向我挥手作别。《诗经•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莫不是我这番隐痛的写照?
其实我并不好奇为什么古人偏好将柳与别离联系一起,但谁又能解心头中仍有挣扎的一番“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呢?
作者简介: 北方,原名文军,敦煌人,业余潜心天水地区古代铜镜研究和文学创作,部分散文、杂文等散见与报刊杂志及网络。现供职于天水市文联。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